數學與生涯發展.經驗分享
作者/張忠謀 (91/11/27)
地點: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生活館二樓201室
主辦單位 : 新竹西北扶輪社--新竹西北國際科技基金會
我們總認為在學時間才是我們的學習時間,以我個人為例,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四年、加上博碩士五年,算一算也有二十一年的時間待在學校,那我到底在學校學到什麼東西﹖「如果你有幸在年輕時住過巴黎,它會一生跟著你,有如一場可帶走的盛宴。」這句話可以形容我前後21年的求學生涯。
二年前,我開始動筆寫自傳,參考了很多昔日留下來的資料,以及三十多年前自己寫的博士論文,結果卻發現很多地方看不懂。後來再重翻過去讀的滾瓜爛熟的大學工程教科書,竟也不太看得懂。當我回顧這幾十年的工作生涯,我發現只有在工作前五年,用得到過去在大學、研究院所學的20-30%,之後的工作生涯,直接用到的部分幾乎等於零。
因此當我說學校生活是「一場可帶走的盛宴」時,指的絕非謀生知識的學習。「一場可帶走的盛宴」這句話出自作家海明威之口,他曾說:「如果你有幸在年輕時住過巴黎,它會一生跟著你,有如一場可帶走的盛宴。」
為什麼我會這樣認為呢﹖我自己分析有三個原因:第一,在學期間是培養求知心最好的時候,換句話,你要把握機會多方面培養興趣,無論是文學、藝術、科學都行,這就是一種求知心。
第二,你必須培養學習的習慣,包括終生學習的習慣。如果年輕人在學期間既沒有培養求知心,又沒有培養學習的習慣,我認為他是在浪費時間,那麼就算他考試考得再好,教科書背得再熟,我都認為沒有用。
第三,培養「思考能力」。學習只是一種input,如果沒有經過內化(internalize)的過程,去發展出自己的思想,那不叫思考。求知心及學習習慣是兩項基本能力,若沒能在求學階段及時培養,完全是虛擲光陰。至於思考能力則是更進一步的能力,如果想做些與普通人不同的事,非具備此能力不可。
事實上,普通人常掛在嘴邊的「活到老,學到老」,並非我所認同的終生學習,因為每個人所堅持的終生學習絕非是泛泛的「活到老,學到老」,而是必需具備「有目標」、「有紀律」、「有計畫」三項要素。
終身學習的第一要素 ─ 訂定目標
終生學習必須設立長期目標,也可稱做終生目標,同時也要有長則幾年、短則幾天的短期目標。舉例來說,我認為每個人都需定下「一定要能跟得上所屬行業」的終生目標,不論是醫生、科學家、工程師,都要跟得上該行業的最新潮流。像我自從出校門後,就一直待在半導體業,因此我所立的終生學習目標,就是要跟上半導體業的發展。當我處在技術的領域,我就要求自己要跟上技術的最新發展,後來轉往業務領域,我的目標就換成要跟上半導體各項業務的發展。
假如你在銀行界工作,能否想像30年、40年前畢業的銀行家,即使是最好學校的畢業生,日常所處理的業務也只不過是存、放款,發行政府公債、賺賺其中的差價罷了,十分簡單。我在美國做事的前十年,常有人跟我說,銀行家是最容易不過的行業,每天下午3點鐘就可以下班打高爾夫球。然而物換星移,現在銀行業的情況與過去相較有天攘之別,因為目前錢可以跨地區、跨時區流通,所以銀行業開始受到全球金融的影響,再過幾年,我相信網際網路對銀行業的轉變將造成更大的影響。倘若你不能隨時跟上最新發展,我看你的不用10年、15年,就會面臨失業的危險,而身處科技、工程領域的人,職業壽命更短。
我踏出校門時,根本不認識Transistor(電晶體)這個字,這不是因為我無知,事實上當時很少人了解電晶體。但是過不了幾年,情況丕變,很多人全都知道電晶體的存在,可見知識是以很快的速度前進,如果無法與時俱進,就只有等著失業的份。因此,人人都該抱持職業壽命目標是:「無論身處何種行業,都要跟上潮流」。
至於短期目標,範圍則大得多,因為它可以是興趣,也可以與工作職務的調動相結合。當一個工程、技術、或研發的人才,被拔擢成為經理人時,他開始需要涉獵財務、行銷等其他相關知識,如果原本沒有這些知識基礎,就要盡快設立短期目標,在未來半年內盡量地學習。這是必要的學習階段,倘若不這樣做,新職務可能無法得到完全發揮,這是每個人在工作上可以經常設定的短期目標。
提到興趣,以我本身為例,有一次我無意間發現,法王路易十四與清朝的康熙皇帝竟身處同一時代,他們可能不知對方的存在,但二人都同是盛世,因國情不同,導致後來發展殊異,這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努力研讀兩人的歷史。而在音樂方面,我建議對馬勒音樂有興趣的人,可以把馬勒的其他曲目也拿來聽一聽,只要是有音樂底子的人,不消幾個月就可成為專家,因為馬勒的作品並不多,不像貝多芬,至少要2年的時間才夠。以上所指的是業餘的興趣。如果你對小說有興趣,也可以針對某個時代、某個小說家的作品,從事短期的研究。
我個人回到台灣已經14年,由於在美國住了30多年,雖然平日喜歡閱讀中文書報,一時之間對久違的中國社會仍然無法全盤認識,我心想既然要回來做事,就一定要深入了解,於是我立了一個短期目標:要在2年內充份了解台灣的政治及經濟。後來發現,我的野心實在太大了,二年的時間根本不夠,我就把時間延長3年,但是直到現在,我對台灣的政治及經濟還是不太了解,這項短期目標就變成我的終生目標。
終身學習的第二要素 ─ 有紀律
終生學習的第二個要素是「紀律」,也就是你對學習要下決心,決定要花多少時間來從事終生學習,因為學習是一件相當嚴肅的事情。以聆聽為例,其實傾聽別人講話也是一種學習。聆聽的要訣首先要「專心」,我在交大授課時,曾用一小時專門闡述「專心聽」的技巧及重要性。一般人的觀念是大家要盡力培養口才,卻忽略了聽的能力對一個人的發展,比講的能力更重要。根據我的經驗,如果聽者能完全了解講者所說的內容,那他聽的效率是100%,可是大部分人的效率卻連50%都達不到。想藉由聆聽得到學習效果,第一個必要條件是專心聽以提高聽的效率,第二個重點則在於你是否能將聽到的內容,經過內化(Internalized)的過程。我隨身攜帶一本小記事簿,這是我的學習工具之一,每當我聽到一些好觀念及資訊,一定隨手紀錄下來。本子的大小需要講究,太大太小都不恰當。這樣做的好處很多,譬如為了知己知彼,我十分注意客戶的財務報表,資料來源很多,因為所有美國上市公司都會對外提供財務報表,另外也可以從Wall Street Journal得到相關訊息,但是這些資料,如果你沒有真正記下來,沒有經過消化,還是沒有用。我有一本標準型筆記本,我在家看財務報表時,一看到重點就趕快記在筆記本,之後每個月或二週溫習一次,就像溫習教科書一樣,這就是internalize的過程。當然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記得全部的內容,可是你一定不會漏掉重點--例如客戶是不是要垮台了﹖還是成長得很快﹖這你絕對會記得。有時當我與客戶談話時,他們往往很驚奇為何我知道這麼多事,我就跟他們說,這些都是公開資訊(public information),只是別人沒有注意到罷了。
終生學習必須有紀律、花時間、嚴肅看待。好的終生學習,絕對會影響生活習慣,我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每天會盡可能看書2小時,閱讀的內容可以是與工作相關的資料,或是客戶的財務報告,也可以做純興趣的閱讀。像我閱讀清朝、法國的歷史,聽聽馬勒的音樂,年輕時每天花4小時,現在年紀大了,只花2小時,周六、周日兩天加起來也有8、9個小時用在看書、聽音樂。這樣一來自然不熱衷應酬,因為有更具樂趣的事情可做。
至於運動,我覺得打爾夫球的運動效率不高,不如每天在跑步機上跑步半小時,這是最高效率的運動,運動量相可抵高爾夫球的好幾倍,可見終生學習的紀律真的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終身學習的第三要素 ─ 有計畫
終身學習的最後一個要素就是要有計畫,學習如果沒有計劃就會事倍功半。所謂的計劃是先設定你的長、短期目標,你要看什麼書、讀什麼雜誌、報紙,或是要跟誰說話都要有計劃。尤其是跟誰講話一定要想清楚,因為生活習慣也跟平常接觸的人具有密切關係,會決定你的交友圈,因此對要認識哪些人也要訂出一個方向。像我對經濟、趨勢的議題一直有濃厚興趣,因此交往的朋友常是學術界、經濟界人士。不過跟這些專業人士交往前,自己要先打好基礎,不然彼此的談話很難出現交集,也就毫無樂趣可言。至於認識這些人的方法,是先打聽好這些人出現的場合,找機會跟他們認識。根據我跟一些經濟學家互動的經驗,常發現報紙上對一些國際知名經濟學家的言論報導常有出錯之處。為什麼我能發現﹖因為我有興趣,平常多有涉獵。
此外,回學校充電也是必要的,即使很忙,每年也應抽出一、二個星期到學校聽課,即使不是正式的上課,也可多參加研討會,一年五到十次,聽的時候要嚴肅地做筆記,才能學到東西。
總之,學校是培養求知心、學習習慣及思考能力的地方,但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個人並不需要進大學,更不需要進研究所才能培養出這些能力。我們常看到一些從學校半途出家的人依然能做出一番大事,而且他的思想、學問比接受正常教育的人來得好,這是因為他們擁有良好的終生學習習慣。
我常問自己一個問題:如何鑑定一所學校的好壞﹖一般的答案是師資好、設備好,在我看來,這倒是其次。我認為一所學校最重要的是學生,要有好同學才能培養你的求知心、良好的學習習慣,思考能力。如果有人踏出校門許久,還在談論自己的學校,除非你那時認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那才值得懷念。倘若只將學校當作一個吸收知識的地方,我是不覺得有何懷念的價值。過去常看到一些四、五十歲,甚至六、七十歲的人,喜歡說自己出身某某名校,每次聽到這種言論,我總覺得奇怪,因為他們給我一種「這些學校很難進」的感覺,換言之,他們將那幾年當成生命的巔峰,以後就都在走下坡路。你會發現,那些會把名校掛在嘴邊的人,他生命的顛峰歲月往往真的就只在考上一所好學校。在座如果誰有此習慣,我勸你最好早點戒掉。
我今日的演講到此結束,有問題歡迎大家提出討論。
Q & A:
Q:董事長畢業於哪個學校?
我是MIT的學士、碩士,史丹佛的博士,MIT並不是一個值得懷念的學校,這句話我當著MIT校長面前說過,他給我的回答是:現在的MIT已經跟以前大不相同,已經能令人懷念了。我個人的經驗是,過去的MIT並不注意培養一個人的求知心、學習習慣、或思考能力,除了技術以外,其他領域的通識教育寥寥可數。我自己的求知能力是在哈佛培養起來,在哈佛的那一年絕對是我生命中可帶走的盛宴。到了MIT以後,除了工程以外,我覺得這個學校實在很單調、無味,而且所學到的專業知識,日後在工作上用得到的地方實在是很少,反倒是在哈佛以及在中學所培養出的好奇心對我來說才是非常重要。
Q: 美台之間的企業文化有何不同?
有二個主要差異點,一是地區的分別,另外更重要的是時代的分別。當美國的企業文化已經邁進二十世紀的下半階段,在台灣,除了少數的高科技公司之外,大多數的企業文化卻仍停留在二十世紀初期。目前台灣傳統的家族企業文化,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找到,台灣只是晚了幾十年而已,但台灣的變遷迅速,現在科學園區的企業文化跟美國高科技公司相比,已經不遑多讓。雖然其中有一些地區性的差別,但是並不重要。以放假來說,台灣很少人度假(vacation),但假日(holiday)很多,美國人則是習慣每年計劃二、三星期的長假。另外,一般人總認為美國的企業文化崇尚參與式管理,台灣則是強權專制式的管理,這種現象與其說是地區的不同,不如說是時代的因素,因為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也是專制式的管理。我最近閱讀1866-1946年間,老福特(HenryFord)管理福特汽車公司的做法,發現他完全採取強權管理,跟當今台灣家族企業的管理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老福特認為自己對員工很好,因為他在1920年代,首開全美風氣之先,將工人的工資從一天2.5美元,提高為5美元,並在公司內部成立員工福利部門,如果員工生病,該部門會派專人探問或送花,任何員工的婚喪喜慶,福利部門的人也會參加,也就是把員工當成自家人看待,這跟台灣目前許多家族企業的做法如出一轍,只是時代至少差了五十年,但是台灣進步的速度很快。1985年我剛回台灣時,那時台灣的科技業尚不發達,仍是傳統的家族企業當道,那時候台灣的企業文化落後美國六十年;到了1999年,我發現園區的科技文化,跟美國的科技文化已經沒有太大的不同,就連傳統工業也在蛻變中,現在跟美國頂多差距三、四十年。台灣以十年的時間趕上三十幾年的差距,再過幾年,也許就不分軒輊了。
此外,敘薪制度(compensation)也是文化差異的一部分,關於這點,也是時代的因素大於地區的影響。我幾十年在美國親眼目睹,compensation制度從以salary為主,變成以bonus、股票為主。1985年我剛回國時,台灣還是以salary為主,當時在美國,股票、bonus的敘薪制度已經十分盛行,算一算,台灣落後美國二十年。但是台灣急起直追,目前台灣的compensation文化已經等於美國1990年的compensation文化,換言之,股票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我必須強調這是時代而非地區的因素。
Q:請董事長闡述思考能力的培養方法。
我一向提倡苦思,思考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對我來說,思考能力就是很苦地去想一件事情,但之前必須要有準備,也就是要準備完備的資料,不然一定會成效不彰。所謂的思考資料來自你平日的學習、閱讀書籍、報章雜誌的心得,並將之內化的結果,然後再進入苦思的階段。所謂的苦思就是要放下手邊一切事務,專心地想。有人邊思考邊聽音樂,這對我來說絕對行不通。總之,思考第一要先有資料,沒有資料的輔助,絕對想不出什麼好東西。
Q:面對當今的聯考制度,許多父母常面臨兩難,不知是該重視小孩的課業,還是該鼓勵他們培養興趣及對知識的好奇心﹖請問董事長的好奇心是來自學校還是家庭的引導﹖
二者都有。學校跟家庭教育一樣重要。現在許多高中生認為考取一間好大學是他們讀書的唯一目標,而念大學的唯一的目標則是拿到文憑,這完全喪失求學的意義。我認為教育制度應該要改,而家庭則也在其中扮演不可忽視的角色。儘管大家對教育制度的不滿聲浪日益高漲,但也有相當多學生即使身處此制度,仍然培養出終生學習的習慣,可見只要有心,制度並不能封殺所有人。當然,制度如果能進一步改善,促成更多人領略學習的樂趣就更好了。
Q:我是一個老師,想請教董事長,教大學生到底要注重深度還是廣度?
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如果是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廣度應該優於深度。可是這有例外。如果有學生對某門學科有特別的天賦與興趣,並已立下日後的目標,他在大學就應該往深度鑽研,像李遠哲院長就曾經說過,他在中學時代就已經確定要當化學家,但像我這樣的人,在中學時代,還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志向,所以在大學最好廣泛涉獵,把深度留到碩士、博士階段。我很欣賞長春藤名校的通識教育,可惜的是,只有長春藤名校的學生可以藉通識教育的訓練,在畢業後找到好工作,如果其他學校的學生依樣畫葫蘆,卻可能面臨失業的危險。我以一個家長的身分,將自己教導小孩的經驗跟大家分享:我將女兒送到注重通識教育的長春藤學校讀大學,現在她不是一個專門的學者,可是她的人生非常快樂,享受很多的樂趣、興趣。她會花時間研究、思考事情,雖然賺的錢不多,也不是什麼專家,可是她很快樂。如果當年她大學畢業後,能夠再多忍耐一點繼續深造碩士、博士,那就可以又有興趣,又能當專家了,可惜她沒有這樣的耐心,大學畢業後就出來了。雖然她現在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可是擁有廣泛的興趣,人生非常快樂,價值觀也很正確。
Q:學歷跟成功有無必要關聯?
何謂成功的定義﹖如果以錢來衡量成功,我覺得錢跟學校學習、終生學習並沒有太大關係,一個人即使沒有學習的習慣,沒有終生學習的成果,還是可以賺很多錢,因為賺錢跟其他因素的關聯性比較大。然而,我深深認為,以錢來衡量成功是一件大錯特錯的事。以我女兒為例,我認為她很成功,假如有人說她不成功,我一定會跳出來替她申辯。因為她的人生既美滿又快樂,儘管她並沒有賺到很多錢。另外,許多我很尊敬的學者,他們賺的錢也不多,可是他們在我的眼裡非常成功。因此,錢不能拿來當作衡量成功的標準。在我看來,只要一個人快樂、滿足,有成就感,那他就是一個成功的人。
Top作者/吳培元 (88/10/1)
不知不覺間在交大應用數學系任教的時間已將近四分之一世紀,這也幾乎是我生命中一半的歲月。在學校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一年年隨著春去秋來,學生們也一批批地畢業,而自己也由一個初到學校的菜鳥慢慢變成一個年高德劭的大老。當初共事的教職員同事,有很多也先後退休或過世,而所教的學生也由當初的弟妹輩演變成現在的兒女輩。這一段伴隨交大成長的過程也將是我成人歲月中最穩定珍貴的時段。
回首前塵,近四十年前的事猶如發生在昨日。我第一次對數學產生興趣應是在建國中學初三上「平面幾何」課的時候。當時的任課老師王德成先生雖是補習班名師之一,但在平常教學還是相當認真的。他每在教完一個段落後,就會指定一些課外問題讓我們回家作,隔一段時間後再在班上檢討。這一類題目總不外是平面上的圖形,如三角形、四邊形及圓等的證明或作圖題,但要解出來卻往往需要絞盡腦汁,利用所學的定義、定理,有時還需要加上輔助線才能完成,其挑戰性遠超過之前唸過的算術、代數等科目中例行的演算題。由解題的過程中我也對邏輯推理的技巧有了初步的理解。到了修課後期,老師給的題目已不足以滿足我的好奇心,於是我又到圖書館中把各種升學用的數學參考書,甚至於數學辭典中的平面幾何問題也都一一解出。這種解題的狂熱一直持續到高一的時候,這應該也是我對數學產生興趣,終致選擇其為終生事業的開始吧。平面幾何問題用途並不是太大,其發展遠自古希臘文明時期即已展開,到了十八、十九世紀已經到了極致,難有繼續推進的餘地,但作為一個中學階段的科目而言,則不失為訓練學生作邏輯思考能力的場址。
考大學時,台大數學系和清華數學系理所當然地成為我的前兩個志願。雖然這與一般世俗價值觀念並不相符(當時的甲組,即自然組,最熱門的科系是電機系。),但我的父母並沒有阻攔我的選擇,這也是我應該要感謝他們的。以我的聯考成績要進台大電機系是綽綽有餘,但我對當初的選擇卻從來沒有後悔過。
台大四年和國外留學五年,對本科倒沒有投注太多的心力,當時年少輕狂,也作了不少荒唐的事,如打麻將、跳舞、追女生等樣樣都來。尤其在美國唸書的那一段時間正是七零年代的前半期,美國社會經歷了反越戰、嬉皮文化的洗禮,社會價值觀正進行著一場驚天動地的變革,中國大陸文革則進入後半段的動亂,而台灣留學生則承受著保釣運動的衝擊,個人在這樣變動的環境中也不免受到影響,在美五年的狂飆歲月將永遠是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段。
我在1975年回到交大任教,教學與研究工作才慢慢步上正途。求學期間只是被動地以通過考試、完成指導教授要求的事項為滿足,在教書後則反客為主,要自己先了解課程內容後,才能傳達給學生,也才能回答學生的問題。我當初專攻的領域是「泛函分析」,更精確的說是「算子理論」,主要研究無限矩陣的結構。回交大的前幾年,為了配合應數系開課的需要,開的多是一些統計方面的課程。這原是我副修的科目,靠著自己慢慢進修,倒也達到了可以作研究的臨界點,只是這一步終究沒有跨過去。一直到今天,早期修過我課的學生仍以為我是唸統計的呢!以後有一段時間,我對離散數學、演算法也很感興趣,開過一些課也參加相關的書報討論,但最後還是回歸到本行的算子理論。近年來的研究課題也牽涉到平面及投影幾何的問題,可以說經過四十年的迂迴,又回到了當初興趣初起時的原點。
隨著應數系碩士班、博士班的相繼成立,系館由博愛校區的教學大樓,搬到光復校區的管理館而科學一館,個人研究室也越搬越大,作研究的形態也由單打獨鬥發展成和學生組成團隊,藉由校外資源,與海外學者交流訪問,共同打拼。作學者之餘也兼作研究計畫的管理者。只是我生性魯鈍,總覺得真正深刻的學術成果應是由個人深思所得,所謂的學術會議、交流訪問等,其扮演的社交功能實大於學術功能(借用當代最有名的華人數學家陳省身先生語)。
這兩年來,因為身兼一份數學專業期刊「台灣數學期刊」(Taiwanese Journal of Mathematics)總編輯之職,也經歷了一番全然不同的經驗。在經常性地處理稿件之餘,邀稿、規劃專刊、爭取經費等也都成了需要思考的問題。眼前的目標是想在完成三年任期後,能讓期刊的水準更上一層樓。
能夠在數學的學術領域中踽踽獨行,應該感謝的人很多。首先想謝謝我在Indiana University唸書時的指導教授John B. Conway。他在我寫博士論文最困頓的期間,實質性地幫我跨出決定性的一大步。他的開朗、寬厚也一直是我欣羨的特質。多年以後,他轉到University of Tennessee擔任數學系系主任,並以此經驗寫了一本獨一無二的書"On being a department head",內容即是教人如何作系主任。前幾年他和一位學生合寫了一篇論文獻給他當年的指導教授,以祝賀後者的退休。今年我也很幸運地有機會和我的一位學生高華隆,合寫了一篇論文作為他六十歲生日的賀禮。另外,我指導過的六個博士班學生(郭昆煌、陳功宇、王進賢、于啟輝、高華隆、辛靜宜)也對我有不少的幫助,他們的激勵也使我更能奮力向前。最後當然要感謝我太太顧燕翎女士,我們由同一學校留學而於同一年進入交大服務,她在女權運動方面一直很活躍,社會知名度也遠高過我,近年來則被延攬到台北市政府服務。我長久以來也甘於作一個成功女性背後的男人。
聯華電子董事長曹興誠先生最近說的一句話深獲我心,他說人生原不必作太多規劃或太逆勢強求,隨遇而安才能處處享受生命中不期而遇的驚喜,這也可作為我今後歲月的座右銘吧!
吳培元教授小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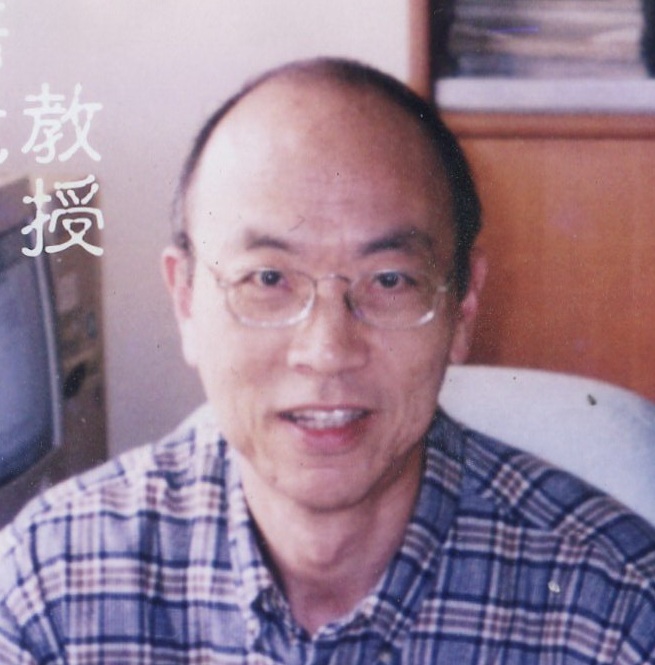
- 1965-1969 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學士
- 1970-1975 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數學系哲學博士
-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
-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系主任
- 1998-2000 兼任「台灣數學期刊」總編輯
作者/林松山 (88/10/1)
壹、求學
受到李政道、楊振寧二位先生的影響,像60年代許多數理好的高中生一樣,大學聯考時我也以台大物理系為第一志願,但放榜時卻進了台大農工系機械組。大一上學期的微積分課程,用的是英文教科書,再加上老師一來就用ε-δ講極限,學期結束時微積分竟在迷迷糊糊中被當掉了。暑假重修微積分,上課的老師是數學所的研究生,講得倒是很清楚,突然間,發現自己好像開竅了。暑修成績居然名列重修生的前茅,在這些研究生鼓勵下,我通過數學系的轉系考試,也就這樣由農機系轉到數學系去。
台大數學系當時還是「過三高當兩門」的時代(大二必修高等微積分、高等幾何、高等代數三個「高等」的課),大二、大三課餘時間我都在古樸典雅的總圖書館中度過。我們班上是台大有史以來女生最強的一班。當今世界上著名女數學家如李文卿、張聖容及金芳蓉皆是班上同學,可想見其餘同學壓力有多大,尤其是男同學。
大四寒假從屏東老家回到台北後,同學轉告我,必修課微分幾何當了一批人,我也是其中之一。想到爸爸媽媽已經準備要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這下子他們的希望卻將落空。接連來的二、三個禮拜,我經常在半夜醒來,瞪著天花板心想「怎麼會這樣子呢?」到老師家求情也數度被推出門外。大四上學期開學後就有不祥的預兆,當時系裡盛傳老師要「品質管制」學生,我也恭逢其盛。我們那屆是服一年預備軍官役的最後一屆,國防部也同意全國當年未能畢業的大四生可先行服役,於是我決定當完一年預官再回台大重修微分幾何。
大學畢業後考上台大數學研究所,主修微分方程,指導老師張秋俊先生,年青有為。研究所畢業時,我被選為數學所畢業生代表,可以上台從校長手中領畢業證書,總算讓父母親在多等了四年後看到這一幕。我的數學系求學經驗,使得我在教書之後,對學習不順利的學生多了一分理解與關懷,也頗能留意到學生家長的謙卑希望。
台大齊聚許多台灣優秀學生,學風自由,社團活動蓬勃(我曾參加登山社及晨曦佛學社),及五花八門的演講。由於我是住宿生,理、工、醫的學生混住在一起,所以接觸的面較廣,除了唸數學外,生活也過得多彩多姿。研二時在法文班上認識了外文三的戴曉霞小姐(目前任教於本校教育學程中心),經過許多努力,終於在她畢業後不久,將她娶入門,多唸幾年台大,對我來說娶到內人是最重要的成就。
我唸完碩士留在系裡當了一年助教,經系上一位澳洲籍教授的介紹到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的Heriot-Watt大學唸博士。他們給我三年的獎學金,在英國三年完成博士學位也是常態。英國是很人性化的國家,例如因我有一年助教經驗,又有眷屬,故獎學金隨之調高。又如當年出國管制很嚴,我出國時,太太尚未拿到入學許可不能一起出國,但英國老師們認為夫妻要住在一起才能settle-down,安心做事。多虧這些老師們的幫忙,我們這對新婚夫妻很快地就在英國重聚,並在如詩如畫的愛丁堡度過美好的三年。
英國的博士訓練是典型的師徒制;不須修必修課,也沒有博士資格考。那年我們新進四個博士班研究生(research student),除了我之外,有二位本地蘇格蘭人及一位伊拉克人。我們每週各自和自己的指導教授正式見面談一個鐘頭的研究工作,每天有三次和系裡老師、同學碰面的機會:早茶(約10點多)、午餐、下午茶(約下午3點多),大家閒聊學界動態、趣事。老師們將學生逐漸帶進了這個行業,讓學生了解傳統及行規,希望學生將來畢業後不致於犯大錯或吃悶虧。我們採quarter制,一年三個quarter,一個quarter約十個禮拜。每個quarter會有一位同領域的老師講一門課;每星期三個鐘頭、零學分的課。另外就是每週五下午四點到五點的colloquium talk,會有一位校外著名學者來講他的工作情形,會後還有茶會,因此我們學生也看過不少各國的名人。
上英國老師的課,讓我開了眼界,也因此知道應該怎樣教書。通常他們選定一個與研究相關的主題,闡明動機,內容由簡入深,逐步延伸出來,並旁及相關領域的應用和未來可能的發展。上課內容經常出現可作為研究題目的素材。一個quarter下來真是收益匪淺。當時的筆記,我還留著,偶爾拿出來翻閱,除了重溫美麗的歲月,也可警惕自己教學的方法是否合宜。在愛丁堡三年我與指導老師合作四篇論文,回國前已經確信自己可以獨立研究了。當時我心想:都學會了編織捕魚網,若非偷懶,怎會抓不到魚呢?
貳、教學
在博士學位快修完前,由台大張老師的推薦向交大申請教職,當時的所長是滄海兄,系主任是國順兄,我很快地得到聘函,來到了交大。
由於個人的求學經驗,使我在教書時很在乎學生的當場反應,並著重向學生介紹學習動機、目的及應用,也試著由最基本素材逐步建構出整個系統來。希望同學能藉此感受到數學由具體到抽象的抽離過程,試圖重構定理發現的歷程,讓同學體會其合理性及必然性。雖然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也不是經常可以做得很成功,一不小心,便會造成進度落後或畫蛇添足的後果。但偶爾見台下原本一臉茫然的學生,突然出現一雙發亮的眼神,就知道小計得逞,也鼓勵我再口沫橫飛一番,努力喚醒其餘眾生。
我一直對大學部學生抱有較多的寬容,甚至於溺愛,因而難免有時需要刻意拉長臉以壓住陣腳。近年來,我發現班上學生家長的年紀大都比我小,加上學生好像愈來愈活潑可愛,一股莫名的「父愛」經常會不經意地湧出。至於帶研究生,我一直以英國師徒制為本,對這些「衣缽傳人」的訓練較嚴厲。早年因個人較不成熟及文化差異的緣故,成效不如預期。直到許正雄君(現任教於中央大學數學系)來交大唸博士班,才開始享受到師徒間縱情論學之樂,許君也在此練就了一付好身手。
參、師友
這二十多年來,我很感謝交大提供一個可以讓我按著自己步調成長的環境,系裡還有許多在各方面可向其學習或借鏡的同事。在國內外對我的數學研究有重要影響者也不下十位,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華人有三位,他們是目前任教於中正大學的林長壽兄(C.S. Lin),新加坡大學及Georgia Tech的周修義兄,及哈佛的丘成桐先生。
1986年我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 San Diego)進修時,認識了長壽兄。他自台大數學系畢業後到紐約大學(NYU)隨Nirenberg教授唸博士,唸完博士丘先生請他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二年博士後研究,丘先生到聖地牙哥時也一起過去教書。年紀比我輕的長壽兄,早以在locally isometric imbedding theorem的工作而名聞學界,我們倆人一見如故,又對純曲量方程式很有興趣,便一起進行研究。當時大家對此在幾何上重要的方程式,了解甚少。
近年來,長壽兄在此方程有非常深刻且重要的結果,並榮獲199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殊榮,他是第一位在國內工作而獲選的數學院士。與長壽兄一起共同研究的三、四個月中,讓我有機會看到一位用全付生命力去追求完美的「藝術家」。他的獨立、自主及創意的特色實在罕見,像他一樣對數學本質有深刻洞見的人也是非常少見的。
長壽兄曾告訴我:「面對數學問題,要去找到它最自然的看法。」他曾談起其成名作的故事:當他還是博士生時,有天到指導老師Nirenberg教授的研究室,看到老師正與訪客討論著locally isometric imbedding問題,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這個題目,但他感覺到老師及訪客的說法很不自然,可能都想錯了方向。幾個月後,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做出解答,指導老師既驚訝又高興,這消息不久就傳遍學界。想不到百年老問題,耗盡多少傑出數學家心血,竟給一位來自台灣的年輕學生用「最自然」的方式解決了。
前幾年丘先生在台灣訪問一年時,曾在他的課上花了十幾個小時重証長壽的「最自然」看法,丘先生一再提到長壽的定理會在數學史上留名。我很幸運曾有機會和這位天才一起做過心靈上的溝通,也因此體會到何謂「數學天份、創意、品味和全付心力的投入」。
1985年我擔任系主任時,曾邀請修義兄來系裡訪問一個月,當時他在動力系統領域上已經是位領導者。修義兄戰前生於上海,後來全家移居新加坡,是道地的新加坡華人。他從新加坡大學畢業後到美國馬里蘭(Maryland)跟Dr. J. Yorke唸博士。修義兄也是JDE主編,Dr. J. Hale的傳人。他為人熱情,做事圓融又富行政專才,前幾年Georgia Tech數學系找Hale與他去領導。目前該系已是學界重鎮,各路英豪的焦點。近年來新加坡大學想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力邀傑出校友的他回去幫忙。他在新大這二年,做了不少革新的規畫,相信假以時日必有大成。他又在1995年來台訪問近一年,在課堂上替我們介紹了動力系統的最新發展且建議一系列的研究題目。他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電機系教授蔡少堂(L.O. Chua)是舊識,他趁蔡教授來交大參加研討會時,介紹我和蔡教授認識。蔡教授很熱心地要我去研究他們胞型神經網路(Cellular Neural Networks, CNN)的數學基礎。因此我與系上莊重、石至文和清華的林文偉三位教授,合提一個國科會三年計畫,以研究此問題。在修義兄的各方面協助之下,我們研究群在動力系統有所突破、有所建樹。今年更帶給我第三次國科會自然處傑出研究獎。修義兄多年來支持我們在國際學術上的活動不遺餘力,真是位良師益友。
1985年丘成桐先生第一次來台,到本校參加「中美微分方程研討會」。美方代表有六人,除丘先生外尚有劉太平先生及Nirenberg 等,皆為該領域的超級巨星。我方主辦人是鄭國順兄,當時我兼系所主管,因此幫國順兄招待客人。丘先生的爽朗、快人、快語讓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在媒體記者訪問時,依然直指問題核心,毫不保留。他不落俗套,天馬行空的想法、看法,讓我這種經思想管制過、受填鴨教育的人感到強烈的震撼。也提醒我要經常去反省、檢討自己的立場及出發點,進而去了解造成自己持此立場及看法的深層原因,對我而言,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經驗及啟發。
見丘先生前,我已獲國科會補助將自1985年8月起赴美進修一年。原本計畫到Wisconsin Madison,丘先生得知後,邀我到他所任教的UC, San Diego。我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再說洛杉磯的迪斯尼樂園及聖地牙哥的海洋世界,對當時我那二位年僅六歲及四歲的小孩來說,實在是好玩多了。
丘先生是公認不世出的天才,他的努力也是超乎常人(從當研究生起,經常保持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以上)。他在數學及理論物理的造詣,對我來說是不見邊際的大洋,我只能望之興嘆。在此我引述他曾說過的一些話:「大自然是以幾何的方式向我呈現,我在幾何的研究就是在研究物理,在研究大向然。」「人是宇宙的一部份,再複雜也不比整個宇宙複雜。」「光用人腦去做數學,總有乾涸的時候,應該多多觀察,回顧大自然。」這些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的治學態度,我也努力張開心眼去看這世界,不再縮在象牙塔裡。
丘先生的父親丘鎮英教授在戰後遷居香港時,任教於新亞書院,專精於中西哲學的比較。丘先生曾說他孩提時代,經常旁聽父親及新亞的學生在家裡開懷暢談古今中外文史,他陶醉在那春風裡,也帶給他爾後能夠綜觀全局、深富史觀的治學態度。多年來,他是我看過對學生最尊重、最寬容、最有耐心的老師。在丘先生回憶鎮英教授的文章裡,經常可看到小時的種種身教對丘先生的深刻影響。丘先生與李遠哲先生同在1997年接受了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從那天起他成為我們的校友,也因此對交大更多了一分親切及關懷。
丘先生目前正在整理鎮英教授的文稿──海山樓詩抄,及他自己在世界各地一些有關數學研究的經驗及教育演講稿。我正跟他洽商是否可由我們交大出版社來出版,讓我們也能分享這份榮耀。
林松山教授小檔案:

- 英國愛丁堡Heriot-Watt大學博士
- 台灣大學數學系學士,碩士
- 現任: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
- 國立交通大學理學院院長
- 教育部顧問室數學顧問
- 國科會國家理論科學中心執行委員
- 國科會1999年自然處傑出研究獎
- 國科會1992年自然處傑出研究獎
- 國科會1990年自然處傑出研究獎
作者/游惠琴 (88/10/1)
大學時唸的是外文系,最後卻成為數學家,1996年自美返台到交大應用數學系任教的黃光明教授,舉手投足間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文人氣息,而其細膩的思維方式、開放的思考空間又無形中顯示出數學專家一貫的特質。
黃教授愛數學,也愛橋牌。他挪挪黑框眼鏡,回憶起幾十年前的往事。他說小時候家裡沒有電視,平時沒什麼娛樂,由於父母親喜歡打橋牌,便教他和弟弟打,結果打橋牌反而成為他們一家四口最佳的家庭娛樂活動。「橋牌運用到很多數學問題,比如說如何打牌、叫牌是概率問題,而安排賽程則是組合數學問題。」談起橋牌和數學,黃教授整個人似乎亮了起來。黃教授高中時加入師大附中橋牌社,與其弟黃光輝在1968、1969年的國際橋牌賽上大顯身手,倆人並為中華代表隊奪得世界亞軍之殊榮。
從小就對數學這門學科情有獨鍾,大學卻唸台大外文系,黃教授笑說:「中學時期,我的數學成績在班上也是佼佼者,選讀外文是因為當時以為自己的興趣在文學,後來才發現自己還是比較適合走數學這條路。」大學畢業後,他赴美唸管理研究所,取得MBA學位後,改讀統計研究所,雖然沒有數理學習背景,黃教授卻能於三年內順利拿到統計碩、博士學位,由此可見其天賦異稟的數學天份。
黃教授表示,一個人要容許自己有摸索、調整的空間,沒有理由在十幾歲時就對自己的一生設限。許多學生在選填志願時,考慮的因素往往是將來的社會出路,而非本身的興趣。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入股分紅制度,吸引眾多學生奮力地想擠入電子資訊科系。黃教授認為,現在社會的變化很大,許多讀商科的學生也很受青睞。他舉例說,在美國商科學生畢業後到華爾街上班,他們賺的錢比其他科系的學生多,但工作五年後多半受不了那樣的環境,因為人生所追求的不僅僅只是一幢房子、一部好車。他感慨地說,「工作是一輩子的事,就像選老婆一樣。你要選『有錢』的老婆,還是你『喜歡』的老婆?」他認為大學是通才教育,學生不可能在大學中學會所有工作上的實際事務,學生在大學裡主要是學習、獲得「有工作的能力」。只要能表現出自己有工作及學習的能力,那麼出社會時,找工作就不是大問題了。
1967年,黃教授進入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一待29年,退休後原本欲赴大陸北京大學任教,至北大前他計劃先到交通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三個月,後來覺得交大環境很好,同仁們相處融洽,學校方面也允許他開許多他有興趣的課,最後便婉拒擁有堅強純數學部門的北大。黃教授到交大任教前,沒有任何教學經驗,由於他本身的主要興趣在做研究,他希望能藉由教學來帶動研究風氣。
黃教授坦白地指出,在美國求學、工作時,一直掛著學人的身份,雖然貝爾實驗室良好的研究環境是全世界眾所周知的,他在學問上也獲得許多成就,但對美國社會則較缺乏實際參與,感覺上有點像外人。回到台灣後,他對台灣社會的關懷度提高,較有參與感。他認為台灣的教育成果不錯,他自己是受完大學教育才出國留學,台灣的教育使他在國外有競爭力,他很感謝以往教授過他的老師。黃教授表示,希望能將在國外工作的經歷、累積的學問傳承給下一代,並且很樂意拾起這支知識接力棒。
黃教授建議對數學有興趣的同學,要堅持走下去,他說只要有興趣就能學得好,擁有豐富的學問後,自然就沒有工作的問題。此外,他鼓勵同學們研究工作可以從早期就開始,他說:「在台灣,大家的觀念是寫博士論文時,才是真正開始做研究,學校並不要求碩士班學生的論文內容要創新。」他認為碩士班學生,甚至大學部學生都可以及早開始做研究。黃教授表示以前開的課都是研究生才能修,這學期他開了一門課讓大二 ~ 大四都可以來修的研究課程。他解釋說:「以『組合學』來說,組合學中許多問題的解決是一步步來的,必須先將小部份問題解決,慢慢累積經驗,才有能力解出大問題。」他希望透過這門課,讓學生不要怕做研究,並破除學生認為要有高深的學問才能做研究的刻板印象。其實「學」和「做」同時進行是最有利的,黃教授認為,從研究中可以發現自己不足的地方,進而加強學習的動機,學完又可馬上做印證,更可鼓動學習的興趣,如此構成一良性循環模式。
黃教授語重心長地指出,應數系許多優秀的大學部學生,畢業後便改唸其他較熱門的研究所,如此恐將造成不易吸收到更好學生的情形,這是目前應數系所有同仁必須正視的問題,大家應該集思廣益想辦法留住好人才。
雖然目前電子、資訊系所的出路較好,但學生若只看到利益面,似乎太過短見。黃教授強調,唯有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才能持久。現階段數學系的出路或許比不上電資科系,但數學終究是基礎學問,幾乎每門學科都會應用到數學,黃教授殷殷期望同學們不要因一時些微的薪資差異,而放棄自己的理想。
黃光明教授小檔案:

- 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統計博士
-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管理學碩士
-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
- 現任:交通大學講座教授、應用數學系教授
- 1967年進入貝爾實驗室工作,達29年之久
- 1996年迄今於交通大學應數系任教
作者/張鎮華 (88/10/1)
我於1988年2月來到交大應數系,在此之前應數系的許多人員來來去去,可謂交大應數系力量的往外擴散,這些人帶著交大應數系的優良傳統,在各處均有優秀的表現,讓我們予有榮焉。1988年之後,應數系進入人事穩定時期,安定中逐漸成長。
交大應數系的離散數學組在台灣小有名氣,這始於徐力行教授的創立。徐教授從在1985年到1988年擔任系主任,這時也正是離散數學人才逐漸回台灣的時期,交大應數系得天獨厚,來了許多這方面的人,前後有:1981年徐力行教授、1985年黃大原教授、1987年傅恆霖教授、1988年張鎮華教授、1991年陳秋媛教授、1995年翁志文教授、1996年黃光明教授。若再加上原來系上的林朝枝教授及劉松田教授,以在職進修的方式攻讀資訊工程博士,我們的離散數學組在全台灣算是最齊全的了。其中尤以黃光明教授的來到交大,對我們最具影響,容後再表。唯一的遺憾是,徐力行教授當完系主任後,因為他原本的身份是應數系和資科系合聘教授,本來都是兩邊各開一門課,任應數系主任時,因公務繁忙,不能在資科系授課,所以在任期滿後,資科系發出最後通牒,希望他選擇一系全時任職,他就到資科系去了;不過他還是常常回來參加應數系離散數學的討論會。
接下來是1988年到1991年由韋金昌教授擔任系主任,這期間有許多重大的事情:籌設統計所、成立工作站室、爭取數學中心圖書服務計畫、以及新助理的來系。
台灣的統計系所多半在商學院,和理科比較有關的,除了中央研究院統計所外,只有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各設有統計所在理學院裡,其他各校數學系有少數統計專長的教授。本系1981年聘請具機率方面專長的蕭正堂教授不幸發生山難,1982年聘的王丕承教授後來也離開了。為增加統計方面人才,我們於1988年聘陳鄰安教授,1989年聘周幼珍副教授和彭南夫副教授。有了這些基礎,遂開始向理學院提出成立統計所的計劃,在當時理學院郭滄海院長(1990年至1993年)的協助下,一方面取得台灣數學界同仁的認同,再則與教育部高教司劉維琪司長討論,終於在1992年成立統計所,由貝爾實驗室聘到李昭勝教授回來擔任所長,系上三位統計方面的老師亦轉任該所。如今交大統計所已經和清華、中央鼎足而立了。
早年系上的電腦多半以PC為主,工作站室的成立是在1991年。當時劉松田教授以資訊的背景來籌劃,目標是設立繪圖能力強的工作站,以協助微積分教學,這個作法在當時數學界算是很先進的。完整的計劃書,得到教育部五百萬元支助,配合系上一定金額,買了一批IRIS工作站,進而成立了工作站室(位於現在的當期期刊室),與微電腦室(位於現在的期刊合訂本室)。
國科會數學中心成立以來,其圖書服務計劃先有台大、中研院與清華,後來加上成大與中山;而新竹因已有清華的計劃,交大就無緣參與。這一直到沙晉康教授擔任國科會自然處長(1989年到1991年)才有轉機;沙處長上任之初即到一些重點大學訪視民情,當時郭滄海教授、林松山教授等大老趁機向他提出要求,他遂以五十萬元讓我們開始,比起台大、清華的四、五百萬元,是少很多,但也算有個起頭。這之前,郭、林等大老亦曾向時任國科會數學審議人的康明昌教授反應,交大數學系以堂堂大校之系,在國科會各委員會竟無代表;所以我剛來交大就銜命到數學中心當委員,這是1988年的事;1991年我到審議會,以後本系在國科會各委員會均有代表,展現出一定的實力。後來我們的圖書服務計劃,經多年慢慢的努力,已調升到二百多萬元,雖然還是不到台大、清華的五百萬元,但也有其半數了。
早年,系上只有惠玲一人幫助系務,後來有臨時的助教葉淑杏,一直到1990年陳盈吟及1991年張麗君來系,系辦公室的運作才穩定下來。後來,又由系上老師的國科會計劃,多申請到兩位專任助理,一掌電腦,一掌圖書,雖然均曾更換人員,但對系上幫忙很大。
韋教授之後,系主任的任期改為兩年,目的在使更多人能人盡其才。邵錦昌老師是這新制度下的第一位系主任,由1991年到1993年。這期間也是本系聚集數值分析人才的重要時刻。早先數值分析方面有林志青教授,但他也是和資科系合聘,最後走了徐力行教授的路,到資科系去了。到了1991年劉晉良教授來系,我們才又有了這方面的種子,後來1992年馮潤華教授,1994年葉立明教授,以及日後若干位研究偏微分方程的同仁們兼做數值研究,我們的數值行列就齊了。
邵主任在任時,曾積極向數學會爭取舉辦年會,並向理學院申請到十萬元的補助,遂有1994年底在交大應數系辦年會一案。早年,郭滄海教授曾任數學會理事(1985年到1987年),後來我因緣際會,於1992年起一直擔任理事。1994年底在交大舉辦年會,由於全系同仁們的齊心努力,空前成功,並創下了首次舉辦年會卻不花數學會一毛錢的例子,為後來的年會立下了典範。同時,郭滄海教授及林松山教授亦順利地進入理事會,交大應數系在數學會自此舉足輕重。現在,郭滄海教授榮任理事長(1998年到1999年),在黃大原秘書長的幫忙下,替數學會做了許多事情。
我在1993年至1995年任系主任,除了辦數學年會以外,印象深刻的有:成立數學圖書分館、招收數學資優生、推甄生,以及促成兩對佳偶。
成立數學圖書分館的構想在我當系主任之前就在談,主要的原因有二:其一、數學中心的圖書計劃要求我們成立圖書分館,以落實服務;其二、圖書之於數學家,正如儀器之於實驗科學家或電腦之於電腦科學家,放在身旁才方便。為了實現大家這個想法,我在林松山教授等人的幫忙下,先找當時圖書館的丁館長商談,並請鄧校長主持,才得以在1994年於交大應數系成立數學圖書分館,也就是現在圖書館閱覽室這一區,此後所有的數學雜誌都搬回來放在這裡,大家用起來方便多了。當時,丁館長是礙於校長批示才同意,所以相對地提出一些條件,例如,只能試行兩年等。總算我們日後努力經營,使數學圖書分館得以順利地維持下來。當時,第一任圖書館管理者是許元春教授的夫人黃素貞,她替本館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一直到她才因為小孩的出生而離職。
台灣數學資優生的制度已行之多年,往年他們都到台大、師大和清華。我任系主任時參加第一次的教務會議,在審查各系招生名額時就發現,我們系上在資優生的招收名額上是零,反而有體優生。經詢問,才知原來我們歷年來也曾申請資優生的名額,但教育部的答案是,「應用數學不是基礎科學」,所以不能加入。我花了半年時間,經常和教育部打交道,並透過師大陳昭地教授幫忙,也請當時理學院褚德三院長(1993年到1996年)協助,終於在1994年三月底,數學資優班於師大集訓前一天接到通知,我們也可以去參加了。於是我就單槍匹馬(因為已放春假,找不到同仁幫忙),獨自到師大和三十位同學一一面談,最後收到五位同學,這就是我們第一屆數學資優生。同年,我們也參加了大學推荐甄試,招收了五位同學。我們的招生遂進入多元化的管道。
另外,促成蔡孟傑教授及劉晉良教授兩對佳偶,更是預想不到的收穫,為本以為乏味的官場生涯加添了調味料,而今回想起來,最得意也就是這兩件事了。
1995年到1997年傅恆霖教授接掌應數系系主任的工作。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環境大整理,以其之前擔任訓導長的行政經驗,將系上整治得井井有秩。1995年底將系辦公室搬到現在的地方,這裡原是統計所的辦公室,那時統計所因空間不足,搬到現在的綜合一館。工作站室及微電腦室則搬到空出來的系辦,並將圖書室打通成現在的樣子,舊雜誌移到原來的微電腦室,現期雜誌移到原來工作站室,外面就成了現在的閱覽室,空間一下子開擴了起來。此外,二樓的老師廁所也加裝了洗澡用具,讓愛運動易流汗的老師們使用。系辦公室外的中庭的沙發擺設,也讓環境生動起來了。
這期間,課程的設計與教學方式,有極多的討論,特別是微積分的教學有了重大的改變。主要的做法是,將各班微積分混班,分成每班約是原來一倍半的中班上課。初時,各系系主任均不安心,害怕微積分也變成普物大班上課的方式,可能產生種種缺失。為了瞭解成效,系上特別請了唐麗英老師幫忙設計問卷,每學期瞭解學生的反應。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數學生們竟然十分喜歡這樣的混班上課方式。現在微積分改為混班小班的方式上課,是後來莊重主任時討論出來的。
1996年暑假黃光明教授由貝爾實驗室提早退休來到交大,是大事一件。他本來要去北京大學主持應用數學所,但是想先來交大看看。我們在沒有名額的情況下,幸得鄧校長大力支持,才聘到黃教授。他研究優秀,為人謙和,並喜歡提攜後進,實在是本系之福。
1997年到1999年是莊重教授主持系務。莊主任勤於溝通,替本系營造出祥和氣氛。這時的交大應數系,可說已經到了比較成熟的階段,創業雖艱,守成更難,前述的種種業務,能經營得當,莊主任可說是表現出極大的功力。
有一項新的發展是「基礎科學諮詢中心」的成立。這始於張俊彥校長當教育部顧問室主任時,交代林松山院長(1996年至今)在交大理學院做的事,應數系亦努力以赴。除了辦座談會,1998年暑假還辦了一次中學數學教師營,由莊重教授、黃大原教授和我授課,頗得讚賞。後來,方向轉向網路教學,向計中借調陳明璋老師來理學院幫忙,應數系非常努力地在做數學網路教學,一年下來,小有成就,最近並已獲得國科會科教處大型計劃的支助。
1999年起應數系由黃大原教授接任系主任一職,以其穩重的性格,我們有福了,且拭目以待吧。
張鎮華教授小檔案:

- 1982年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運籌學)
- 1974年國立中央大學理學士(數學)
- 2001至今,台灣大學教授
- 1988-2001年交通大學教授
- 1983-1988年中央大學副教授
- 國科會數學學門審議人(80-81年,83-85年)
- 交通大學應數系系主任(82-84年)
- 交通大學副教務長(87-89年)
- 80-81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 83-85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